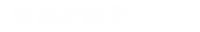瑞恩高斯林 疫情期间 我和全世界最酷编剧成了密友( 四 )
琼斯仍然记得考夫曼几年前在晚宴中跟他讲过的一部当时在创作中的小说。他仍然能清楚地记得那顿晚餐的所有细节,他也记得当时正在与考夫曼交流这部小说时的他有多么激动。但那段记忆对他来说也“像梦一样离奇古怪”。琼斯告诉我:“那些想法……嗯我真的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从此他们就像梦境一样占据了我大脑的一部分。”
“是关于电影档案的吗?”琼斯问我。“他们还在吗?”
我开始和琼斯谈论这本书。一个58岁的,特别高傲的学术影评人B. Rosenberger。Rosenberg在曼哈顿上城的学校教授电影研究课。他为了关于一部黑白默片的专题论文出差到佛罗里达,但他在偶然遇见一个卧病在床的百岁老人Ingo Cutbirch后决定放弃他的项目。老人用尽一生在公寓里拍摄定格动画。Rosenberg抓住了这个机会并把它视为是个有潜力的非主流艺术。考夫曼以一个讽刺的“白人救世主”口吻在叙事。故事中的Rosenberg把自己视为是一个发掘黑人艺术家的伟大人物。
罗森博格看了整部电影。这是一部关于宇宙、时间流逝和未来南北内战的电影,中间穿插着两个喜剧演员之间的竞争,最后上升到谋杀。电影里有一只驴和一只叫钙的大蚂蚁。这部电影持续三个月。当罗森博格还在看电影的时候,老人去世了。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在野心和虚伪驱使下,Rosenberg把行囊装上卡车准备搬回纽约将Cutbirth的遗作发展成一种文化。然而卡车在途中着火了。当Rosenberg从昏迷中醒来时,所有东西都被摧毁了,而他也早已忘记了整部电影,只留下了唯一一张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镜头画面。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只占据了前80页。我向琼斯解释说,安特金德有700多页长。
“我的天啊,700多页!”琼斯惊呆了,看得出他对此也十分兴奋。
书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让我觉得恍恍惚惚。比如罗森博格的内心独白离得很近,让人觉得有点窒息。他试图修复过场电影所遭受的荒谬挫折。他失去了工作和房子,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一个非理性和虚无的目标。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羞辱和嘲笑。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似乎像流行病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受挫。这本书就像导演考夫曼的自我批评,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希特勒式的“可悲的自恋者”,或者更直白地说,一个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权利和能力的人。
作为一个批评家,Rosenberg与喜剧基本无缘。他否定喜剧,认为那是荒谬的并具有暴力色彩的:就像在华纳兄弟的戏剧卡通中表现出的一样,一只郊狼总是被暴力对待而走鹃的反应永远是幸灾乐祸地笑。而现在他的处境变得和喜剧中的郊狼一样,他所受到的痛苦都被当做是人们的笑料。
"我最终得出结论,我的生活是一场荒谬的闹剧。"罗森博格最后说道。“所有的不幸和遭遇,甚至毁了Ingo电影和我一生的那场大火,都是一场闹剧。更可怕的是我的想法和记忆。他们总是那么愚蠢可笑。我就像一个小丑,有时候我很清楚。我可以看到,我生命中的那些时刻,就像一个旁观者,是多么可耻,但我无法控制那些时刻。”
“很多故事或剧本都是创作者经过一段时间后,以回忆的方式写出来的,”考夫曼很久以前告诉我,“以回望的方式去了解过去。就像牙疼一样,那种疼痛目前会对你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当你多年后再想一想,在饭桌上和朋友聊起牙疼的时候,你就不再受这种疼痛的折磨了。你可以把这种痛苦作为一个故事讲给朋友听,但在牙疼的过程中却做不到。这是一个特别混乱的时刻。”
考夫曼所讲的点在于,他很努力地在创造一种不那么完美的叙事,想让故事背后的意义成为一段秘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梦境般虚幻的元素。就像《纽约提喻法》中那栋着火的房子。这些画面像是在他意识边缘存在的梦境,但对考夫曼本人来说,这种叙事是关乎于现实主义的。他说: “这让我能感觉到我在讲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推荐阅读
- 张忠德、林定坤入选2021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
- Dota2-骗完礼物就跑路?ok林仔惨遭遗弃
- 下庄脐橙细嫩化渣 余味清香——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向你倾情推荐
- doinb怒撕拳头设计师瞎设计,林伟翔吐槽薇恩皮肤设计
- 吉林市中心医院举办吉林省吉林地区呼吸学会交流会
- 林七七终于在虎牙活动中线下见面,君泽眼里只有林七七
- 夜读丨林清玄:如果老是看着船尾,生命的悲怀是不可免的
- 松花糖、芝麻糖、麻通、麻球…桂林人记忆里的甜蜜年味
- 林草日历?|北京乡土树种:栾树、酸枣、拐枣
- 林农因竹而富 广东广宁林下经济融合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