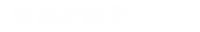瑞恩高斯林 疫情期间 我和全世界最酷编剧成了密友( 三 )
2011年,一位出版编辑问考夫曼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小说,考夫曼觉得自己可以从中解脱出来。既然写任何剧本都不能当真,那就写点别的好了:比如写一组叫Trunk的特朗普动画小说;或者在北美中部增加一个新的山脉,然后让小说的主人公和这座山发生性关系。他不得不写作。虽然他已经40年没有认真写散文了,但他一直在用自己的风格写剧本,尽管他无能,大胆的新尝试被假想敌欺负。尽管有声音说你真的不能这样写,考夫曼还是强迫自己坚持自己的风格。他说:“我必须继续这样下去,直到我被打败。”
直到听他讲述电影《改编剧本》的创作历程,我才真实地体会到这一点。故事是这样的:他同意改编苏珊·奥尔琳的《兰花窃贼》。原着是关于兰花和一个佛罗里达的偷花贼却不遵循正常情节的故事。他不知从何下手。在数月的“重抑郁”后,他最终摆开原着,开始思考当前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鲜活的事情。
偷兰花的
最后这部电影聚焦在了尝试改编《兰花盗贼》的考夫曼身上。在开场的一个镜头里,我们看的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夫曼挥舞着奥尔琳的书,对着好莱坞高管说他不想“把性、枪、‘速度与激情’,或是主人公学到人生重要一课,或是九九八十一难后的胜利塞进。书上不是这样写的,生活不是这么进行的,一切都不是这么好莱坞的。”这一幕真实还原了考夫曼在接手电影前对好莱坞高管的解释。
在初稿中,我讨论了考夫曼的创造力,并把他描述为绕道而行,在绕道上写他想写的东西——这似乎让他很痛苦。
我最后问他:
“你为你的信仰受苦吗?你有没有想过让自己轻松一点?”他有没有想过写动作片什么的?
他回答道:
“我想赚钱。我告诉自己:我能写出票房大卖的大片。”但他也知道这是自我安慰,他从未尝试过。他想写原创的、影响深远的作品,这让他很自豪。他告诉我:“有很多不健康、极端的烂片,不真实,没有人文元素,让人走下坡路,误入歧途。我不想拍一部烂片。”
斯派克·琼斯曾执导过《改编剧本》和《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傀儡人生》。他拿考夫曼和坎耶·威斯特一起比较。他有些犹豫,讲的结结巴巴。琼斯对我说:“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比较,因为大家对威斯特众说纷纭。”琼斯和威斯特共事15年了。他说:“不是威斯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一旦他误解了别人的意思,就和所有人一样会很受伤。但他身不由己,我觉得考夫曼和他处境一样。再说一次,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比较,因为他们俩在其他各方面都差很多。”然后他沉默了好一阵,试图接点别的话。
说实话,我采访的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对考夫曼的钦佩。杰西·巴克利在《我想结束这一切》中说:“我猜考夫曼是我见过的最像古希腊神的人。”你什么意思?她说:“作为一个人,他太漂亮,太脆弱。但他也不是那样的。嘿,也许我不应该描述他。”考夫曼最好的朋友演员凯瑟琳·基纳出演了他的三部电影。她在面试前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她不能很好地描述考夫曼。电话采访前,她有点崩溃:“如果你能看到我的脸,你就会在我眼里认识考夫曼。”不用看她的脸,我就能从她温暖的语气和坚定的决心中看出。她说:“考夫曼和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但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认为他可以和任何人交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剩下的,只能理解,不能说。最后,她只能说:“考夫曼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是有意离题的。我强调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有点担心考夫曼和我的对话不能被正确解读。读者可能会不耐烦地翻阅这篇文章,厌倦考夫曼和他坚持从一个非常复杂的角度解决一个琐碎的存在主义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听这样的对话是很感人的。他的脆弱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反而会产生同情他的欲望。
推荐阅读
- 张忠德、林定坤入选2021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
- Dota2-骗完礼物就跑路?ok林仔惨遭遗弃
- 下庄脐橙细嫩化渣 余味清香——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向你倾情推荐
- doinb怒撕拳头设计师瞎设计,林伟翔吐槽薇恩皮肤设计
- 吉林市中心医院举办吉林省吉林地区呼吸学会交流会
- 林七七终于在虎牙活动中线下见面,君泽眼里只有林七七
- 夜读丨林清玄:如果老是看着船尾,生命的悲怀是不可免的
- 松花糖、芝麻糖、麻通、麻球…桂林人记忆里的甜蜜年味
- 林草日历?|北京乡土树种:栾树、酸枣、拐枣
- 林农因竹而富 广东广宁林下经济融合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