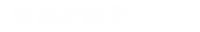瑞恩高斯林 疫情期间 我和全世界最酷编剧成了密友
原创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考夫
MAN
2020
傻瓜
KAUFMAN
翻译卡尔文·黄
微博@cal堃
“所以他们让我重写?”查理·考夫曼问。
我解释道,是的。两周前我提交了关于查理·考夫曼的故事稿件。就在刚刚我收到杂志主编的反馈,情况不大妙。
61岁的查理·考夫曼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他的作品以超自然和疯狂的自我指向而闻名。1999年,他的作品《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傀儡生活》让他大受欢迎。我写他的故事是因为他的第一部小说《安特金德》于7月7日出版。
我最初计划在三月份的一个周三飞去纽约去采访他,但是我所在的华盛顿州附近突发的疫情使这个计划破灭。
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正如我在故事初稿中写的:
所以,我们每周三开始交谈一次,通常是半小时或更长时间。我不止一次建议中途休息一下,但考夫曼说他会继续。考夫曼说:“我说得越多,就越现实。”我每周都能在固定的时间和他聊天,感觉很棒。
我家附近的疫情趋于好转,考夫曼所在的纽约开始情况不妙,他又恰恰独居在高风险区。每周三我都会先问他怎么样。考夫曼都说“一切照常,但我在想下一步要干嘛”或是“我感觉病毒找不上我,但谁又知道呢”或是“一切都好吓人”。有一周他和我说他摔破了他的眼镜而且还原不了,他问我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我会怎么做。有一周我问他怎么样,他扑哧笑出来,我也笑起来。然后他问我怎么样。一阵子后笑声戛然而止,他说:“我害怕。”
我们这样谈了八个星期。在很少有机会去探索生命的新鲜度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去认识一个陌生人是很奇怪的。我们之间发生的不仅仅是友谊和治愈,还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两者兼得,互为受益。4月29日,在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中,考夫曼说:“我们聊得很开心,但我们最终能见面吗?”
我说:“我也在想。这段时间,你我的友谊是我的唯一,甚至超越了亲情,这有点奇怪。”我和他说,我尝试每周和家庭朋友通话,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考夫曼说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有朋友想和他谈谈,但他通常感到焦虑和不舒服。上周有人纠缠他,最后他回答说:“不行,真的不行。”但是考夫曼说和我说话很棒,他不会那样对我。
整个初稿就差不多是这样。故事发展得很慢,有点怪怪的。但是这样写缺乏时间顺序,所以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还是把我们的对话呈现出来,这样更能体现我和考夫曼之间的联系。听起来虽有点荒谬,但是这样写就仿佛疫情期间我和考夫曼生活在一起。
考夫曼在《纽约借代》的片场
问题在于,自我投身进故事创作的两周内,街头游行愈发激烈。主编对我说,这个世界不太平,我写的好像是巴洛克时期的内容,和这个时代脱节了。这样的不协调是不是该改改呢?在收到很多难懂的建议后,我决定再和考夫曼取得联系,最起码让彼此知道发生了什么。
考夫曼大胆地说出了主编的意思:“他们认为我们的故事已经够过时和奇怪的了。他们想让你再和我谈谈,因为你写的东西和现在的游行不合拍。我认为你必须明确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两周前。”
我说道:“我不觉得这是他们的意思,他们不是说没有关联。”但我不确定这样讲够不够诚实。在那个时候,除了很少事情外,我觉得每件事都和我没有关系。
考夫曼愿意接受这个“无关紧要”的意见。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应该谨慎一些。他不能保证自己会一直谨慎。他出书,我写他的故事——即使他觉得不舒服,他也觉得值得。他说:“我现在感觉很好,因为我喜欢你,和你聊天很开心。但是就因为我出版了一本书,你会为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的故事缠着我到7月5日吗?这让我有点尴尬。”
推荐阅读
- 张忠德、林定坤入选2021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
- Dota2-骗完礼物就跑路?ok林仔惨遭遗弃
- 下庄脐橙细嫩化渣 余味清香——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向你倾情推荐
- doinb怒撕拳头设计师瞎设计,林伟翔吐槽薇恩皮肤设计
- 吉林市中心医院举办吉林省吉林地区呼吸学会交流会
- 林七七终于在虎牙活动中线下见面,君泽眼里只有林七七
- 夜读丨林清玄:如果老是看着船尾,生命的悲怀是不可免的
- 松花糖、芝麻糖、麻通、麻球…桂林人记忆里的甜蜜年味
- 林草日历?|北京乡土树种:栾树、酸枣、拐枣
- 林农因竹而富 广东广宁林下经济融合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