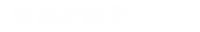如果小说的省略能给读者带来浪漫的想象或诗意的怀旧,那是好的,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省略中,我们看到的是虚幻的道德程序。失去细节记忆和逻辑扭曲后,真正的情感也失去了灵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宫廷遇露西再为爱晕倒,酒店遇卡顿为爱而死”的情节。在这个紧张的包转计划实施之前,狄更斯安排露西再次晕倒,并陷害她去乞求卡顿救她的父亲,至少避免了三层女性道德败坏的嫌疑:一是吸引人们的牺牲;第二,一个已婚女人乞求一个自己的崇拜者在道德上有些腐败;第三,如果你张开嘴,激烈的话语会破坏她温柔的形象,伤害你最好的朋友。所以,在危险面前晕倒,说明露西的善良缺少一种主动的人性。她只是呆在原地。即使丈夫要被送上断头台,她也只是在女性规范的范围内行动,遵守女性道德。“像露西这样只负责晕倒和解决问题的女性形象,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有很多,几乎每部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缺乏温柔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习俗束缚的结果。太多的禁忌和扭曲将人性之美封存在露西的女性形象中。即使狄更斯在小说中接连设置了三个追求者,分别映衬了露西的纯真、圣洁和女性美,但小说中高呼仁、为力而晕的戏剧性话语,更像是套用了传统道德理想和现实价值标准对善与美的公式,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抒情直截了当、粗制滥造,与狄更斯笔下“伟大灵魂”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朱宏在评论《双城记》时说:“那个‘多余的人’卡顿最后哭了,与其说是为爱而死,不如说是在人道主义的眼泪中死去。”这从侧面指出了道德情感的精神缺失。
实际上,萨克雷在其《彭坦尼斯》序中也抱怨过小说家所受的限制,说“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最充分地描写一个男人。我们不得不遮遮盖盖,赋予他以规范化的品格。我们的社会就是容不下艺术中的自然”。虚伪道德波及语言习惯,甚至到了破坏作品艺术性、灵性的程度,这在男性人物形象中存在,在女性人物形象中更为严重。《双城记》塑造的完美露西形象一直被道德传统和现世价值支配着,成为“夫道中心”的附庸物、妇德闺范的蜡像。狄更斯有计划地剥去露西身为女性的“真实”,用乡规俗约道德的“虚幻”来填充,以适应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主流读者的阅读取向。而在经过俗约标准的雕刻后,被剥去和省略的不再是浪漫,不再是对读者余韵想象和解读空间的尊重,相反,简单的二元对立、天使形象的平面夸大是对艺术思想价值的软化,是在经过明丽的包装后灌输给中产主流读者的一碗道德迷魂汤。
露西形象的典型特征是出生在长期的男权制度下,她的“幻觉”来自于长期男性中心的压迫。在“何”的叙事力量下,露西走上了“贤惠”女性的模板,接受着虚假道德的打磨,成为被市场和时代所追随的教科书经典和仁爱典范。每个人都愿意认可她无瑕的道德善良,却没有人记得“她”被淘汰的“女人”的存在逻辑和生存基础。中心话语权力的笔杆刻意省略了“她”的历史和精神,进而逐渐抹去了“她”作为时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和情感。完美露西形象的诞生,意在满足传统的道德理想和现实价值标准,让这个形象实现它的“美”。小说的讽刺之处在于,当“世俗之美”成功时,媒介空但粗糙的幻影美形象阻碍了“她”在人性的花园里自由歌唱,剥离了“她”、“真美”、“真善”的权利,抽走了“她”足以“不昏”的生命力,使她
二、经验改造下的丑:家庭不幸与感性历史观
了解狄更斯的人都知道,狄更斯的家庭生活充满了起起落落,但他一直重视家庭的完整。狄更斯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需官,年薪200多英镑,足以算是当时生活滋润的中产阶级。狄更斯在英格兰南部的查塔姆度过了他最美好的五年童年,然后他的家人经常因为他父亲的挥霍无度而陷入困境。为了谋生,他甚至在12岁生日那天被母亲送去皮鞋和油厂当童工。这段经历对他伤害很大。狄更斯的母亲对她的孩子漠不关心,作为家里的长子,他得到的照顾很少。他体内积累的愤怒影响了他后来的婚姻和家庭。当他设法与一位年轻、美丽、温柔、随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妻子和家庭主妇生活在一起时,他逐渐发现妻子凯瑟琳才华平庸,性格古怪,这对他的创作生涯毫无帮助,这让他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每天都感到阴郁和烦躁。后来,他在自传《大卫·科波菲尔》中提到了这些不幸的经历。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导致他在书中安排了朵拉的早逝,结束了一场夫妻无法提前适应彼此的悲剧。
推荐阅读
- 合肥近视手术价格一览表:如何选择眼科医院去摘镜?
- 摘果子去!万宁山根镇大石岭村圣女果红了
- 华新草莓采摘地图来啦~爱吃草莓的你还不快冲!
- 新春走基层 | 罗平镇:草莓采摘园 拓宽致富路
- 做思想上的“原创者”
- 温州这项农村工作成绩显著,两地摘得“全国先进”!
- 临川区第一人民医院独立完成髓核摘除术(图)
- 草莓现摘现吃小心腹泻
- 协商议政谋良策 履职为民“好声音”——白城市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委员发言摘登之一
- 90后夫妻携手摘镜过新年精准ICL晶体植入助力重返高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