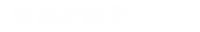比尔德 玛丽·比尔德的剑桥生活:多少学者一起才能买台咖啡机( 二 )
我早上9点骑自行车去部门。路程花了20分钟,因为我比别人慢一点,但是在路上,我一直在想后面的课。到的时候应该多准备一点课,但是和学院的一个同事开会讨论教学计划。剩下的时间差不多够我在10点上课前多抄一页分发资料了。
10点,我和120名大一生谈论了波斯战争和东方主义。有多少人读过爱德华·萨义德?没人读过。
11点,和博士生呆了一个小时,前一天晚上看的是他的作品。12点钟,我的一位哲学大师来和我讨论罗马自由民研讨会,他将在两周内就此发表演讲。
因此,在我们19世纪历史项目的周例会上,我迟到了,部分是因为我去餐厅买了个三明治,打算边走边吃。我们讨论了两篇前达尔文主义文章,关于女性之美,内容十分精彩。但我必须在会议结束前溜出去,这样才能在2点回到学院,开始两个小时的面向3名大二本科生的辅导课,内容是关于罗马宗教,今早第一件事就是读了他们的论文。
下午4点,我刚好有时间查看邮件。自从我上次检查邮箱以来,我已经收到了大约50封电子邮件。之后还要坐车去车站,赶5: 15的火车,去伦敦参加一个校友活动。来回的路上,我仔细看了一篇投稿到期刊上的文章,因为我帮忙修改了这篇期刊上的文章,第二天还看了一些关于招聘面试和教师教学委员会的信息。晚上9点52分回家,11点半前到家,处理完积压的邮件,开始阅读另一位博士生发来的卷帙浩繁的作品,但到了凌晨1点,我很快就筋疲力尽了,于是上床休息——我计划早上7点再工作..
是的,我承认,那时我喝的酒已经超过一个饮酒单位的量,即超过现在推荐我们中产阶级职业女性饮用的酒量。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考试公平吗?
这是一个学术假期。当我飞往芝加哥大学讲课时,我们的学生正在把巴拉克·奥巴马和米兰·昆德拉的材料翻译成拉丁语和希腊语,以提高他们的语言技能。我没有骗你。在我们这个时代,麦考利被翻译了,或者说丘吉尔是幸运的。但我认为拉丁语只会让奥巴马听起来更像麦考利。
在这里度过夏季学期,脑海中总会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我们让学生考试的目的究竟在哪儿。在考试业已与准确性客观性绑定的而今,再没什么比学校的考试事宜更让人觉得糟糕的了。考试导致的双重束缚显而易见。考察的孩子越多,需要的考官就越多。在不发达的过去,只有少数几个孩子会考高级水平课程考试,于是我们有睿智且经验丰富的考官来批改学生答卷,批改他们对格莱斯顿与迪斯雷利优点对比的看法——我们信任批改结果。
考生越多,越难找到足够多的考官,考官经验越少,资质越差,需要密切关注是否符合要求。一个完全安全的解决方法是做选择题。这样,即使是计算机也能准确地纠正它。但如果不是选择题,那么每道题都要有一套可以接受的答案,交给每个考官。这样你甚至可以找实习老师批改试卷,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考生的答案和标准答案进行对比匹配。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压制想象力、独立思考、新奇创新,压制任何敢于写出不属于标准答案的可怜孩子。“不是标准答案”等于“没分”。在不发达的过去,我们依靠智慧、富有经验的考官,区分古怪愚蠢的学生与创新聪明的学生。这是项无法保证精准度的工作,有时考官会出错或者不那么睿智富有经验,但是我们信任他们。
没有机械的手段,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如何进行大规模的考试,这最终相当于降低了标准。
相比之下,剑桥学生是幸运的。
我们都承认考试不能检验所有的能力,我怀疑考试的成功需要某种重男轻女的因素。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评价方法”:学术论文或其他论文。但是考试确实测试了一些我们重视的能力。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在批评获取知识、高效记忆、调动所学、回答问题和恰当辩论的能力。而且我们的考试在测试这些方面也不差——它们像你希望的那样公平。
推荐阅读
- 咖喱猪排饭,健康实惠比外卖强百倍,孩子们吃得开心极了
- 面条这样做,爽滑筋道又好吃,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 王者荣耀:新英雄暃的战斗力天下无双,比吕布还要厉害
- 咸蛋黄肉松烤饭团,香喷喷的营养又好吃,比外卖的健康实惠
- 王者荣耀:又一t0辅助诞生,坦度比肩张飞,控制不输墨子
- 做面包麻烦吗?香甜松软,比卖的好吃
- 吃这四类药物开车比醉驾还危险!开车的人注意
- dnf:全服唯一一把狂战士专属光剑,比光炎剑还罕见
- 梦幻西游:堪比服战号的59级花果山,总价值100万
- LWX打比赛不厉害的时候,才是FPX最强的时候,这句话果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