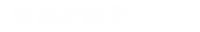于娟视频 新冠康复后 我们一家从法国搬到了新加坡( 三 )
我会再次想到这个病的原因,因为受中国疫情影响,和很多中国朋友一样,我们第一个出门戴口罩。每次戴着口罩出门,都需要鼓起勇气面对质疑的目光和躲闪的人群。其实应该害怕和羞愧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
当然,大部分民众也只是被政府舆论牵着鼻子走。从2月初疫情初起,法国政府关于要不要戴口罩、如何保证口罩供给,就上演了各种政治闹剧,更不要说前期对疫情的低估和整个抗疫过程中决策的低效。而持续了一年的黄马甲运动,史无前例的退休改革大罢工,都让我感受到近乎窒息的社会氛围。尤其是看到那些本地年轻人消极无望的眼神,我更加坚定了带着孩子离开这里的决心。
然而,目前,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坚持每一顿饭,熬过每一个艰难的夜晚,是我们唯一的任务。
也不知道得病的两周是怎么过来的,只觉得每一天都很长,但终究一切都有个尽头。
疾病是骑马而来,但步行而去。虽然我不再发烧,但我总是没有精神,人们有点生病。生病后,我仍然和父母说话。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担心。我们每天都被微信问,怕会有后遗症。经过我的再三安慰,他们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放松,也表达了对我们一家回到亚洲的支持。
不过,好在我们一家人都康复了,有时想想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守在家里便是最大的幸福。“封城”后每天在陪伴孩子和琐碎的家务中度过,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家,窗外熟悉的街景,偶尔也冒出过岁月静好、不再折腾的念头。可是,对于在外漂泊的人来说,到底哪里才是家呢?掐指一算,这是我在法国搬的第7个家。从学生宿舍,到自己租住的studio,再到一家人的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从郊区到市区,再到郊区,又迁回市区。尽管折腾、疲惫,但每一次搬家都满怀着对未来居所的憧憬,期待一个更好的家。
然而,在这片美丽而浪漫的土地上,却缺乏文化和精神的归属。虽然有各种失望,但这个地方终究不是我的安心。
然而,“封城”令下各种手续的办理都遥遥无期。
5月11日,法国“封城令”结束。领事馆和外交部工作的逐步恢复也给了我们一些希望。我们文件的翻译、公证和双重认证程序开始推进。但由于当时机构的工作时间因疫情而缩短,加上之前积压的工作,处理周期大大超过了平时的时限。
还记得我去中国领事馆取新办护照的那天。那是我在巴黎解封后第一次“出远门”,竟有几分激动,反复确认了时间和路线才上路。往日拥挤繁忙的地铁站冷冷清清,站台地面上贴了间隔站位的标志,广播里播报着“新冠病毒依旧在,请大家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地铁车厢里的相邻座位之一被贴上禁止坐的标志。看着车厢里不多的人,无一例外的带着口罩,我脑海里浮现出两个月前的场景——同样的站台,同样的车厢,唯一戴口罩的我像异类一般,接受着来自全车厢目光的“扫射”。原本不易察觉的傲慢与偏见在疫情下暴露无遗。没想到,两个月后,这一切都变了,望着车厢里一个个口罩上方无表情的眼睛,我简直怀疑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
巴黎地铁上戴口罩的人
领事馆门口早已排开了“长龙”,与周围清冷的街景有点格格不入。查证件,量体温,过安检,经过层层关卡,我进入领事馆,拿到了新护照。
在疫情期间,香榭丽舍大街摇摆不定
材料一一办妥后,我们又卡在了新加坡工作准证上,在疫情下,新加坡一度停止了工作准证的签发。我们戏称进入了打游戏通关阶段,而在疫情下,打着当前一关的我们却不知道下一关何时开启。
推荐阅读
- 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康复出院 “白衣战士”画新作:“相信阳光离我们不远了”
- 物品检测到新冠病毒阳性一定会传染给人吗?事实是……
- 45分钟出核酸结果!冬奥场馆全面应用生物气溶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
- 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共同努力
- 新冠概念股远大医药治疗重症新冠临床研究获重要进展
- 上海又有16例新冠患者治愈出院,在院人数屡创新高,出院后将做好健康管理
- 河北手绘“新冠”作品走热 医学科普出新意
- 新冠肺炎十大症状是什么? 为何频繁变异?最新防控知识宝典来了
- 英雄联盟手游官博公告曝光,下周发新春拜年视频
- 张文宏:今年年底可能结束新冠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