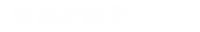陈寅恪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 三 )
1958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了这么一张大字版的海报,说他在教《白元诗证史》时考证很枯燥。他曾经考证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妓女有多大年纪,他在长安是什么样的妓女,甚至考证过白居易当晚没有登上她的船。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作者认为,这完全是捏造的。他找到了当年课堂笔记的残页,证明陈寅恪教授《琵琶行》时,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论述了这首诗所反映的唐朝社会。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字海报里的故事好像没有排好,因为陈寅恪以史学著称的《白元诗话》里也有类似的考证。这个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一段文字引起的。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不避嫌疑登上女子的船感到惊讶。——这是宋人的道德心,不值得和他讨论。没想到,陈寅恪认真关心这件事。他认为洪迈对诗歌的理解有问题。所谓“我们把船移近她的,邀请她加入我们”的“船”,是“我,主人,已经下马,我的客人已经登上他的船”的“船”,而不是“要去江口守护空船”的“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女子登上他的福建船,而不是白登女子的船。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历史学家对诗歌的解释肯定是荒谬的。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作为一种创意,是值得肯定的,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谈诗的心思有点太实际了。比如学者说“天气好”,气象学家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温度,什么是风。这种方式不值得推广。
陈寅恪《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着,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着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主题之外,让人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像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风格独特。他总是习惯于先介绍一些史料,然后再加上评论。给人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未经加工的读书笔记。胡适曾在日记中评价:“当然是今天最深刻、最有见识、最会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确实写得不好。”这不仅仅是胡适的印象。很多人可能也有同感。陈寅恪用文言文写文章,但他的文言文确实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的文章不是很高明,主要集中在文言文的标准上。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尴尬,因为他们不习惯白话文,文言文不够优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绝不是分支的终点。
陈寅恪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的信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推荐阅读
- 刘自超:种植红叶石楠 让日子红红火火
- s26打野刺客大变天,刘备阿轲跌落t3,连招简单
- 刘老实(小小说)
- BLG发文祝贺辅助选手Crisp刘青松LPL登场五周年
- 三孩妈妈刘梅:有三个孩子,将来老了有人陪
- 三国杀:主公武将主公技加强,刘备“激将”强化引人注目
- 刘学州的寻找亲生父母之路
- 梦境修炼皮肤选谁最赚,上单选吕布,辅助选刘禅
- 王者荣耀:新版本吕布出装思路,黄刀吕布被削弱,刘亦菲代言热血
- 南阳市骨科医院关节科刘洋: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