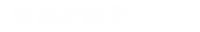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茶的祖籍是在西南地区,贵州发现4000年前的茶籽化石 。现在仍生存的云南勐海县黑山密林中的野生大茶树,树龄约1700年,树高32米,可谓茶树之王了 。
最早,茶是作为治病的药物,大约与“神农嗜百草”的传说有关 。茶由野生发展到人工栽培,在西汉时期 。
从晋到南北朝,茶树的栽培才沿江而下,传到江南,而到了唐代已渐普及全国,“天下尚茶成风” 。
著名的茶的研究学者陆羽、卢仝便是唐代人 。每诵“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句,使我想起当时是用清冽的泉水烹茶,茶叶煮熟味必苦涩,不一定合乎现在人的饮茶习惯 。
宋代民间茶肆林立,我去开封,曾去樊楼故址访古,怀想当初汴梁勾栏、瓦舍和茶楼的流风余韵,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一问,方知东京的陈迹,经过几度黄水泛滥,早埋藏在地下两三米处了 。
对茶道,我是外行,所知仅此而已,不敢炫惑欺人 。婴儿是喝奶水成长的,与茶无缘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第一口茶的,记不清了 。
童年时代,我生长在镇江,大人吃茶,我也跟着吃茶 。当时一点不懂得茶叶有许多学问,饮茶有许多讲究,喝的究竟是龙井还是雨花茶也不知道 。
记得那时每逢伏天,父亲便在家门口设缸施茶,供过路的穷苦人解暑 。我想那茶叶一定好不了,绝不会是毛尖、雀舌 。茶杯从不消毒,人人拿起就喝,也没听说过闹肝炎 。
镇江江边有家“万全楼”,最近我去察看,原址早已不存,仅有一块基石:“万全楼旅馆” 。据邻人说:楼早毁于火 。
当时,大人去吃早茶,常带我去 。讲究的人自己带茶叶,这时才听说“龙井”这名字 。茶博士的胳膊能搁一摞盖碗,他手提铜壶开水,对准茶碗连冲三次,滴水不漏,称作“凤凰三点头” 。
其实,我那时心不在茶,而注目于眼镜肴肉、三鲜干丝和冬笋蟹黄肉包子,吃完这些还得来碗刀鱼面或鳝丝面或鸡火面,肚子填满,然后牛饮几大碗茶解渴而去 。
离“万全楼”不远,还有家“美丽番茶馆”,当时是所谓“上流社会”的时髦交际场所 。
有一次,用罢奶油鲍鱼汤、牛排,端上一杯墨黑的茶水 。我的塾师冬烘先生见别人往杯里加牛奶、加糖,也如法炮制,不料竟错将盐当糖,呷了一口,不禁皱起眉头勉强咽下喉咙,再也不敢喝了 。
事后,塾师对我说:“番菜好吃,可最后这杯又咸又苦的洋茶,实在不敢恭维 。”这种“洋盘”笑话今天听来还以为是故作惊人之笔呢 。
镇江的对岸是扬州 。素知扬州人泡茶馆和泡澡堂子是两手绝活,流行一句谚语:“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
我年少时仅去过扬州一次,亲戚邀我上闻名的“富春花局”吃早茶 。当时这爿茶馆还是一座旧式的瓦房院落,摆设了许多花卉岔景,前前后后挤满了茶客,据说六都是盐商和买卖人谈交易 。
“富春”的茶叶与众不同,讲究“双拼”,杭州的龙井与安徽的魁针镶成,既有龙井的清香,也具魁针的醇厚 。
它的点心最精致,拿手的是三丁包子(鸡丁、肉丁、笋丁)、三鲜煮干丝、干菜包、烫面蒸肉饺、萝卜丝烧饼、翡翠烧卖、千层油糕等等,包子的美味至今过半个世纪了依然为之垂涎 。干丝讲究刀功,薄薄的一片豆腐干能切成二十片,再切细丝,切得细才入味 。
最近我又去了扬州一次,“富春”还是“富春”,可是点心的质量下降了 。
另外,扬州的“狮子头”,确比镇江高明,考究细切粗剁,肉嫩味鲜,团而不散,入口即化 。扬州人取笑镇江的“狮子头”扔过江来能把人脑袋砸个大鼓包,言其坚硬而肉老 。这是题外话了 。
我在南京读中学,星期天也和同学上夫子庙吃茶,什么奇芳阁、六朝居、魁光阁都去过 。我的目的不在饮,而在吃 。
茶馆供应的茶叶不讲究,那几家的点心也不如扬、镇,但是清真的煮干丝和牛肉面不赖 。我喜欢用长条酥油烧饼蘸麻油吃 。这样的烧饼不输黄桥,至今向往 。泮池的秦淮画舫上也卖茶,不过那里以听歌选色为主,醉翁之意不在茶也 。
后来到了上海,我一次也未去过城隍庙湖心亭的茶馆,更不敢上大马路和四马路的茶馆,那是流氓“白相人”吃“讲茶”的地方 。
南京路“新雅”每天下午开放二楼茶座 。广东馆子不兴喝绿茶、花茶,我叫一壶水仙、菊普或铁观音,慢慢品茗 。“新雅”的广东点心也很地道 。
一到四点钟,茶座上经常可以遇见文艺界的朋友,包括30年代的“海派”作家、小报采访人员和电影明星之类 。相互移座共饮,谈天说地,有些马路新闻和名人身边琐事的消息,便是由茶余中产生而见诸报章的 。
有时谈兴未尽,会有熟人提出会餐,愿“包底盘”下馆子吃一顿,五六个人也不过四五元钱 。
苏州人也爱坐茶馆,多半是“书茶”,是为听评书、弹词而每日必到的老茶客 。这种茶馆遍布大街小巷,而我却爱上“吴苑” 。这里庭院深深,名花异草,煞是幽雅,似乎不见女茶客,也不卖点心,闲来嗑嗑瓜子而已 。茶馆毕竟是男人的世界 。
我在广东住的时间较久,不但城市到处有茶楼,农村四处也有茶居 。
广东人饮茶是“茶中有饭,饭中有茶” 。珠江三角洲的耕田佬是每天三茶两饭 。
解放前是早、中、晚都有茶可饮 。
天刚发亮,就有人赶去饮茶了 。如果一个人独溜,先在茶楼门口租一叠小报慢慢消遣 。老茶客照例是“一盅两件”(一杯茶,两个叉烧包或肠粉、烧卖、虾饺、马拉糕两件),花费有限,足以细水流长 。
午茶实际是午餐,除了各式茶点外,添售可以果腹的糯米鸡、裹蒸、炒河粉、伊府汤面、什锦炒饭等等 。
广东朋友常说;“停日请你去饮茶”,实际算是最经济的请吃便饭 。也有的只是一句随便应酬话,我也碰到这样的“孤寒佬”,晚茶都在晚餐之后,旨在朋友之间白天忙了一天,饭后休息休息 。更晚的是十点以后的“宵夜”了 。
广东茶点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不像北京、天津一年四季的豆浆、油饼、果子 。点心是推着车子送上桌的,随意开列几种:咸点如彩蝶金钱夹、肫片甘露批、脆皮鲮鱼角、香葱焗鸡卷、栗子鲜虾酥、鲜菇鸳鸯脯、煎酿禾花雀……甜点如生磨马蹄糕、杭仁莲蓉堆、鲜荔枝奶冻、云腿甘露菊、冰肉鸡蛋盏……另外有小碟豉汁排骨、凤爪、鸡翼等等 。
真正考究饮茶的是粤东潮汕和闽南人 。饮茶就是饮茶,一般去人家做客,主人捧出紫砂小壶、白磁小杯和安放茶具的有孔瓷罐,随饮随沏,步骤有:治器、纳茶、候汤、冲煮、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八道程序,真是讲究到家了 。
壶内茶叶放得满满的,茶汁之浓似酒,缓缓地呷,细细地品,醇厚浓酽,清香甘芬,饮后回味无穷 。
闽南人非常考究叹茶(叹即品赏赞叹的意思),茶叶用的是乌龙,讲求安溪的铁观音或武夷山岩茶,几乎天天饮、时时叹 。所以人说:“闽南人有因喝茶喝破产的 。”我到了泉州、厦门,方知其言不虚 。
抗战时期,我有大半时间在四川,东西南北的主要县城几乎跑遍 。四川人惯饮沱茶,这是一种紧压茶,味浓烈而欠清香 。
四川到处有茶馆,山沟沟的穷乡也不例外 。茶馆只卖茶,不卖点心,是名副其实的喝茶 。
沱茶很经泡,一盅茶可以喝半天 。有人清早来沏盅沱茶,喝到中午回家吃饭,临走吩咐“么师”:“把茶碗给我搁好,晌午我还来 。”“么师”便将他的茶碗盖翻过来 。撂在一边 。
因此,茶可以上午喝,下午又喝 。这种茶客可谓吝啬到家了 。
茶馆是“摆龙门阵”的地方 。人说,四川朋友能说,可能是从“摆龙门阵”练出来的功夫,也许有此道理吧 。
四川茶馆也是旧社会“袍哥”们谈“公事”的场所 。那时代,某些茶馆是与黑社会有联系的 。
有一次,我独自去川西北彝族地区办事 。到了江油中坝,当地人说:“再往山里去,路上不太平 。中坝镇子上商会会长王大爷是这一带的‘舵把子’ 。这人爱面子、讲交情,何妨去看望他,包管你沿途有人接待,平安无事 。”
果然,我每逢在墟场的茶馆歇脚,马上店老板就上前恭恭敬敬地连声问好 。临走,我开销茶钱,店老板硬是不收,说是:“王大爷打了招呼 。你哥子也是茶抬上的朋友,哪有收钱的道理?二回请还来摆嘛 。”
我正纳闷,长途电话也没这样快,店老板是咋个晓得的?原来抬滑竿的伕子已被叮嘱过,让我一进茶馆就坐在当门的桌子口上,自有人前来照料 。他们当我也是“袍哥大爷”呢!
谈到这里,我始终没涉及北京的茶馆 。为什么?我在北京前后住了四十多年,说实在的,除了若干年前去中山公园长美轩、来今雨轩和北海漪澜堂、仿膳喝过香片之外,一次也未进过其他茶馆 。
现在公园里久不卖茶了,有的只是大碗茶,太没意思,对不起,不敢领教 。
【舒湮:坐茶馆】
推荐阅读
- 怎么叫坐浴 坐浴解释
- 42岁殷桃坐高铁惹争议 站车门口摆拍自信秀腹肌
- 我的世界电脑版怎么打开坐标
- 累了,要坐下来,静静地品一杯淡茶
- 人流手术后需要坐“小月子”吗
- 喝茶对长期坐办公室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
- 7坐车超载一个小娃娃怎么处罚
- 久坐便秘怎么办 久坐便秘吃什么好
- 坐品沉香茶偷得半日闲
- 孕妇,坐月子,哺乳期的宝妈可吃的食物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