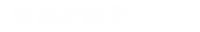不仅如此,《我们属于同一个世界》还呼应了上世纪60年代的“爱与和平”主题和约翰·列侬的“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但它所吸引的受众不再是国家认同之外的个体,而是隐含着欧美发达国家强化的国家认同意识。至于慈善演出或“慈善演出”的形式,则有1971年甲壳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发起、拉维·尚卡尔、埃里克·克莱普顿、鲍勃·迪伦等人参加的“孟加拉难民救济音乐会”的先例。不同的是,前者基于个人的自由表达,保证了整个项目的诚意和可信度。“我们属于同一个世界”恰恰说明了流行音乐文化的世界性取向的衰落,这意味着以艺术自由为代表的乌托邦冲动对社会解放和平等起到了示范作用。
因此,《我们同属一个世界》与其说证明了英美为主导的流行音乐代表着全人类的爱与正义,不如说是新型的媒介帝国权力的展示。斯特劳直言,以摇滚乐文化政治的脉络为参照,很容易就可以将这一系列慈善演出项目指认为“无聊乏味,参与者借此谋取私利,暴露出现存地缘政治秩序的不均等症候,在政治上颇不合时宜”等。但在他看来,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如何通过反思去确定流行音乐在政治上的有效性。或者说,流行音乐文化的话语运作会以何种方式去定义和评估政治介入行为。
【我们同属一个世界 从“乐队赈灾”到“一个世界”:流行音乐的世界想象及其断裂】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现场援助。
不难看出,作为六十年代摇滚乐“盛况”的亲历者,这些英美学者本身也面临着历史断裂的威胁——他们希望诉诸于六十年代摇滚乐的“本真性”来批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的“虚假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样一种反差最终促使那些忠于六十年代理想的学者们转向以“流行音乐”为其总称的研究 。必须看到,根据各自所身处的社会历史境遇,论者们对这同一系列音乐媒介事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英国文化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和马丁·雅克就认为,“乐队援助”表明了一种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情绪,“它确实使人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对他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关注,而撒切尔主义则助长了自私和偏狭。” 不过,麦克盖根则注意到相反的解读方式:“民族优越感和缓解心灵压力感的慷慨尽管易于带来欢乐,但却与撒切尔之回归‘维多利亚价值’保持一致。”可见,流行音乐文化不仅关乎审美,更与政治、道德和社会组织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联合国、流行音乐和“我们”的地位
在通行的历史叙述中,作为“我们同属一个世界”之呼应与“回声”的“让世界充满爱”,标志着中国终于借流行音乐文化与世界实现同步。然而,就在这种“同步”和一往情深又不乏进取的姿态发生之际,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断裂或转折也悄然发生。
1982年,第3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1986年定为国际和平年。1985年12月3日至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1986和平年”研讨会。根据会议通讯,参加会议的所有各方“一致认为和平意味着从个人到集体的非军事化。”但有趣的是,中国各方推出《让世界充满爱》演出的动机,恰恰是“献给世界和平年”。如果说在冷战对抗时代,“国际”无疑意味着“阵营”的“这一面”,而“世界”往往与“自由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两次事件带来的军备竞赛,不仅拖垮了苏联,也催生了一把不可避免的悬在今天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在拥抱“世界”时,“非军事化”的矛头被吞下,在“国际”与“世界”的转换中,一场主体想象的历史逆转与“还原”顺利发生。
推荐阅读
- 连烧数月难寻因 河南小伙肺毁损 医生耗时一个月摸到发烧“开关”小伙写千字长文妙语连珠谢医护
- 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母亲是怎样的体验?
- 一个女人,如果她什么都懂,那她一定恋爱过
- 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是什么感受?
- 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都有哪些表现?
- 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男方和女方各是如何说的
- 女生遇到渣男怎么办?
- 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康复出院 “白衣战士”画新作:“相信阳光离我们不远了”
- 一个剩女的自白:一个人站在寒冷的冬夜之中,输的一塌涂地!
- 南瓜无需烤箱,只要几种简单的食材,一个小锅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