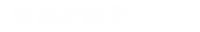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难言的创伤,抑或,世界本身就像诺基亚广告中互相触探的那两只手:近在咫尺,却再也无法彼此触及。北京时间2020年4月19日凌晨开始,前后持续八个小时的“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线上演唱会,于中文社交媒体上传播之时,简单的英文标题大多时候并未被译成中文。偶尔闪现的译名并不统一:“四海聚一家,为世界加油”,“同一个世界:团结在家”,“同一个世界:四海聚一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同一个世界:一起在家”线上演唱会海报
看上去,这些说法之所以显得别扭,原因恐怕首先在于,此处的“家”因其泛化与抽象而显得有些矫情:无论在逻辑还是现实层面,表演者、传播者和观看者其实不大可能聚于“一”家,而是各在自家。“团结在家”听上去也有些怪怪的:要是世界能被团结在家里,那么列侬和洋子的“床上和平”早该宣告实现,世界本身则将显得完全多余。更何况,居家隔离的漫长日月里,“家”或许也并不像是电视剧和广告里那般,显得无比光鲜温馨和富有吸引力吧?
预览中的通用场景转瞬即逝。表面上看,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纽约的主办方“全球公民”明确宣布了版权限制,最终遵守了媒体行业的规则。直播结束后,只能以零星的片段走向世界。所以,那些看“霉”、夸“滚石”、揣摩各家各户室内装修风格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反映出世间悲欢不相通,所有人都被孤立在“家”里的悲惨境遇。虽然有人将演出无法实现全球同步归咎于互联网的客观情况,但事实上,掌握英语可能是进入这个“一个世界”不言而喻的资格和前提。这样,世界名义上的“认同”不就是否定音乐作为一种普遍语言的一种方式,确认了世界的分裂吗?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称:“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回想一下演唱会直播期间,散布全球的观众们窝在家里,隔着种种品牌和尺寸的电子屏幕,大眼瞪小眼,臊眉耷眼的样子,这两句话愈发值得深思。
事实上,能够卖情的流行音乐走到这一步,真的很难怪病毒。“世界”的孤独与疏离,既是社会解体的征兆,也是音乐文化内在悖论与失衡的必然表现。所以“单一世界”这个从未被翻译过,也从未被一个世界直接直面过的意义,有了互联网,就成了无法逃避的现实,重要的不会是“不如从前”的感觉和自信从何而来。在于如何在社会历史语境中重新把握“流行音乐”“我们”“世界”的耦合方式。既然演出本身明确指向上个世纪的宏伟,又不怕其中隐含的貂皮更新风险,那么简单的历史回顾和梳理就有必要见证历史。更重要的是,只有批判性地审视传说中的集体记忆,才能找到重新开始的方式和机会。
“世界”始于一场误会
每当追溯“流行音乐”的历史“复兴”时,人们往往会提到“让世界充满爱”这一大型集体表演。据当事人回忆,此次演出的直接刺激或“灵感”来自于1985年迈克尔·杰克逊等人发起的“我们就是世界”,以及罗大佑、张艾嘉在中国台湾省举办的两场音乐会“明天会更好”。在当时的汉语语境中,前者常被翻译为“天下一家”或“四海一心”/“四海一心”,而后者则常把自己比作前者的回声。有趣的是,“天下一家”或“万国一心”的翻译因其主题模糊而具有普遍性而非“私人性”,但却涵盖并超越了活动
推荐阅读
- 连烧数月难寻因 河南小伙肺毁损 医生耗时一个月摸到发烧“开关”小伙写千字长文妙语连珠谢医护
- 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母亲是怎样的体验?
- 一个女人,如果她什么都懂,那她一定恋爱过
- 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是什么感受?
- 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都有哪些表现?
- 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男方和女方各是如何说的
- 女生遇到渣男怎么办?
- 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康复出院 “白衣战士”画新作:“相信阳光离我们不远了”
- 一个剩女的自白:一个人站在寒冷的冬夜之中,输的一塌涂地!
- 南瓜无需烤箱,只要几种简单的食材,一个小锅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