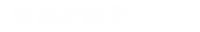坐在一张斑斓的虎皮上
作者:黎荔

以前养过一只虎斑猫,黄棕色的底色,夹有纯黑色的斑纹图案,头部圆润,肌肉发达,两只耳朵总是立着的 。 眼睛大而明亮,呈圆杏核状,颜色在黄色、金色至绿色之间变幻流动 。 买回家不到一年,就养得又肥又大,它的额头上有个黑色的M字母,那黑线条既细又均称 。 整个形态,像个胖乎乎的小老虎,可爱极了 。
有时抚摸这只小老虎的斑纹皮毛时,我会想到丛林中比它硕大和可怕百倍的同族兄弟,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有“万兽之王”和“万兽之皇”称呼的老虎 。 强大、勇猛又血迹斑斑的老虎,精神饱满,穿越林莽和清晨,将足迹留在一条条河流的泥岸 。 三百公斤的庞大体重,使它的梅花状足迹,如此清晰地烙印在滩涂上 。 真想在万杆摇动的竹丛里,在各种鸟兽惊散的纷飞中,辨认老虎的道道花纹,感受它华美颤动的皮毛裹盖的骨架 。
【坐在一张斑斓的虎皮上】在这个世界上,迷恋老虎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正如叶公之好龙 。 我就是其中一个 。 “耽耽老虎底许来,抱石踞坐何雄哉” 。 父亲常常和我说起,他幼年遇虎的事件,当然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了 。 那时候的故乡小城,环城皆山也,山多杂树荒草,亦多走兽飞禽出没,一般的如果子狸、山鸡,吓人的如野猪、大豹、老虎 。 在三反五反中被靠边站的我们家,避乱躲入深山居住,破烂的竹木屋周围是荒山野岭、林深草密 。 秋天的一个早晨,十岁左右的父亲推开竹芭门,看到门前因昨晚下雨打湿的泥地上,清晰地印有一长溜有大有小的梅花状足迹,这足迹沿深山小路而来,向河滩边断断续续延伸而去 。 当时年幼的父亲并没有觉得异常,却见到那村口的大树下,黑压压地聚了一大群人,在那里交头接耳议论不休,“老虎”两个字在人们口中不断地重复着和传递着 。 后来,才听说昨夜一大一小两只老虎从深山出来,入村拖走了猪狗鸡鸭,半夜时分有人从屋顶亲眼见到了这两只老虎 。 那天夜里,老虎就从屋外走过,与父亲之间不过隔着一道破烂的竹芭门 。 祖父祖母异常惶恐,不久之后就带着父亲,从深山中迁出回到街上生活了,即使在街市生活有另一种恐惧压顶 。 我喜欢让父亲一遍又一遍给我讲这个老虎的故事,我托着腮百听不厌 。 老虎,老虎,在猜测它的世界时,它变成想象,变成恐怖的美丽,而不再是漫游在大地上的野兽中的一只 。 那丛林巨兽的身上,可爱的黄黑斑斓,是光线,是毛发,我梦想用渴望的手将它轻轻抚摩 。

后来,我读到名臣言行录外集里这样记载:关学一代大儒张载在京中,坐虎皮说易经,忽一日和二程(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谈易,深获于心,第二天便撤去虎皮,令诸生师事二程 。 这个故事真有趣,少喜谈兵、抱负远大的关中少年张横渠,昂然入京师讲学,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 。 在众人簇拥中,他坐在一张纹彩斑斓的大虎皮上,指点江山,纵论阴阳,以虎虎的目光,讲生气虎虎的易经——想想都觉得霸气侧漏!在张载的身下,一匹好大的虎啊!变幻着朦胧的光明、模糊的黑暗和那原始的金黄,它就像背驮着一座美丽的小山一样,承载着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张载 。 但是,在见到二程之后,张载告诉别人说:“(他们)对《易经》的理解透彻,是我所比不上的,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 。 ”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 。 他与二程纵论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 ”是什么让张载有一把推开虎皮椅的决然,因为他忽有一天,发现了比剑还强、比军事还强的东西,那就是理 。 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地研习理学 。 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 。 这个故事真的是诗——虽然书上说那是理学家的事迹 。 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样一个人,因为那样一张讲座,迷人漂亮的虎皮讲座,后来又被一把推掉的,这一片虎皮的斑彩,这个追求真理的既张扬又谦逊的求道者,使素黯的历史扉页都辉亮了起来 。 他炳炳烺烺,如一只儒门的虎 。
推荐阅读
- 好品山东|一张张“土”生“土”长的地域名片
- 想要生活五彩斑斓,就不能总是一成不变的生活
- 《战地2042》第一赛季将只有一张新地图
- 人人都有一张嘴,但说话,怎么说话能彰显一个人的人品
- 【烂根】栀子坐在石头上,再也不烂根! 杜鹃架在木头上,再也不积水!
- 一张照片能暴露多少隐私 你在群聊中发过原图吗?
- 静坐在夜色里,窗外的风雨已停,思绪早已在书本中徜徉
- 槐花满屋飘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自制美食,带给家人温馨的
- 我偷偷给外婆拍了一张照片,到现在成了我思念她的一个寄托
- 原神:玩家用一张图概括1.0-2.7版本的内容,夜兰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