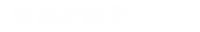由此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我们能在阳文手印或者阴文手印所在的遗址里同时找到这7类符号吗?正如我们所知,桑人相信,他们栖身的岩厦和洞穴中的岩石表面,是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幔帐或薄膜。由于他们把绘制手印作为沟通不同世界的一种方式,再加上这些手印与他们在岩画中绘制的内视图形符号以及其他萨满图像有关系,也许欧洲岩画遗址里的手印可能也有类似的功能。总的来说,大约能在40个遗址里找到这种手印,另外还有我们正在寻找的7类符号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标准提高到有两种符号外加一个手印,那么,符合条件的欧洲岩画遗址的数量就会下降到17个。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标准设置为至少有3种符号加一个手印,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下降到12。遗址中有2种或3种符号,这对于遗址数量的影响并不大,但无论拿这两种标准中的哪一个进行筛选,我们面对的资料数据都是那么有限,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欧洲已知的冰河时期岩画遗址总数已经过350个。
但是我们要记住,在欧洲有手印的岩画遗址很少,所以有这种符号组合的遗址并不多。我们知道,手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岩画中大量出现。因此,手印不太可能在后来可能绘制萨满图像的地方找到。这种情况要么是早期生活在欧洲的古人类并没有真正参与萨满祭祀活动,要么是他们对洞壁和手印的理解方式与桑人完全不同。说得复杂一点,在我讨论过的几个遗址中,岩画的时间跨度很长,那些手印和符号大概是在不同的时期画出来的。与其说是一种辅助信息,我更担心的是,引入手印作为衡量标准,只会让很多东西更加不清晰。但是让我们尝试添加最后一个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是,内视图形符号是否会与人和动物合体后的形象一同出现。然而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共存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并不单单体现在数字上,事实上,在拥有人与动物混合体图像的很多遗址里,同时也发现了更多种类的潜在内视图形符号。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法国东南部那个着名的肖维洞穴,你可能会记得那里有一个画像,是欧洲野牛的头部连着一个女人的身体。肖维洞穴里还有我们一直在寻找的7种符号中的5种,分别是交叉平行线、半圆形、点、平行线和手指刻画的凹槽线条。此外还有阳文和阴文两种手印。在冰河时期欧洲岩画遗址中,肖维洞穴可能是能够证明萨满教理论成立的最佳范例。
另一个看似理想的例子是位于法国中南部的佩什-梅尔洞穴遗址。我们讨论了在那里发现的一系列野牛-女性形象,佩什-梅尔洞穴中也有五种潜在的视觉图形符号,它们与小微岩洞穴中的完全相同,那里也有男性手印和女性手印。接下来我提到了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三友洞的野牛人形象。三友洞与众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动物和人类混合的“巫师”形象,除了野牛人形象之外,还有雄鹿的头和人的身体。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五个符号,那就是在小尾岩洞和史培-梅尔洞发现的五个符号。虽然没有男性手印,但有几个女性手印。
奇怪的是,在这三个遗址内找到的5类符号,形状几乎完全相同。虽然这些遗址在其他方面差异很大,但在这一点上却极其相似。更为吊诡的是,这5类符号齐刷刷地出现的情况仅限于这三处遗址,而其他遗址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在同样位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加尔加斯洞穴,那里确实也有7类潜在内视图形符号中的5类,不过却是锯齿形符号代替了交叉平行线。那个遗址里有超过250个阴文手印,却没有一个阳文手印,也没有动物与人合为一体的图像,使得这里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的标准。不过总体上,加尔加斯洞穴仍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例子。此外还有加比卢遗址,我们已经在圣日耳曼-拉里维耶尔女郎项链的鹿牙上找到了一些符号,其中很多符号和符号组合就出现在加比卢洞穴内部。加比卢洞穴里正好也有两个动物和人合二为一的图像,同样为野牛头人身。但是这里没有任何手印,也不存在大量的潜在内视图形符号。在加比卢,我们只找到了交叉平行线、点和成组的平行线。然而,由于点和线的分布如此广泛,再加上解释方法多样,总的说来,这个遗址似乎不太能证实萨满教理论假设。
推荐阅读
- 健康丨被列为明确致癌物,这种细菌我国有超一半人感染!
- 附魔羊皮纸 7.0幻化 :附魔幻象之书所需的材料一览
- 陶泽如电视剧 老戏骨陶泽如 再次出演电视剧《激荡》 大半人生奉献给表演
- 格斗游戏《幻象破坏者:Omnia》2022年3月15日发售 定价39.9美元
- 夏威夷之恋 《夏威夷之恋》逼真的现实乃是幻象
- 澳男去野外钓鱼,竟然被半人半狗的生物跟踪,还拍到了照片
- 魔兽世界:9.1.5“夜之子”幻化,变身苏拉玛守卫,这不是幻象
- |魔兽世界:9.1.5“夜之子”幻化,变身苏拉玛守卫,这不是幻象
- 64岁女造型师专为中老年女性扮美
- 放皇子和放猛犸,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和TI10迎来了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