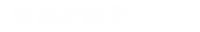陈司翰在看守所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想我的时候看看天空,也许我也在看。”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刚接到判决,李荣惠的姐姐们担心她得抑郁症,每天轮流守着她。五姐总是开导她,“昊儿幸好还捡到一条命,判就判了。”她不能接受。
早年,丈夫在开阳县工作,她经常不在家。她忙于工作,但从未想过让祖母或姑姑照顾她,或带陈司翰一起去办公室,或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来照顾陈司翰。她认为这是她作为母亲的职责。陈司翰调到瓮安后,她每天晚上都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况。她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她已经做了所有她应该做好的教育,但是没有人告诉她如果孩子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
后来,李荣惠和五姐开车回瓮安,到陈泗翰的二伯家取同学们给他写的联名求情信。她们目睹了另一起校园暴力,“就在旁边一个小巷子里,几十个学生围着一个孩子打,还有这么长的西瓜刀,他们就你一脚我一脚地踹,那个小孩脸上都是血。”两个人在车里哭成一团,五姐把车开到二伯家楼下,让李荣惠赶紧进楼再报警。她们想到陈泗翰,那天是不是也被这么多人围着打?
第五个姐姐说:“就是从那天开始,姐姐想通了。至少我儿子还活着。”
李荣惠庆幸儿子还活着,可不该儿子背的罪,她不希望就此留在儿子档案里。李荣惠找了几十个律师,都跟她说八年判得过重,却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申诉材料寄到黔南州检察院,几年下来,光打印费就花了上千元。始终没有回音。
唯一一次,州检察院给她打电话,“李荣辉,把你的材料拿回来”。当她到达新建成的大楼时,地板很亮,可以反映出这个数字。她从值班的小女孩手里接过材料,下到大厅时,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一次,李荣辉真的很想放弃。但哭过之后,我想起了在少年犯管教所的儿子。“我们都放弃了,没有人帮助他。”
少管所里的优等生
陈司翰说他不记得李明明的样子了。被打那天,他总是低着头,避免看他们。第二天,我从手术中醒来,得知了李明明的死讯。他在病床上哭了。他说不出当时的感受,这是极其复杂的。他既害怕又难过。他对李明明感到内疚,不敢相信自己从此“手上沾满了鲜血”。
过去的十五年,他都是最循规蹈矩的那类孩子。在少管所,父母、代理律师都问过他,未来有什么计划?他说想继续读书。案子进展不乐观时,他一开口还是说想读书。父母、律师都感慨过,“孩子是不是被关傻了?”
对他来说,这是他最熟悉的事情,也是确定自己还是以前的样子的方式。
2017年8月,陈泗翰的同学第一次到少管所看他,他们刚高考完,陆续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李荣惠带了三个同学进去,她记得陈泗翰那天很开心,一直在笑。月底的亲情电话,陈泗翰第一次主动让她寄课外书过去。也是在那一年,陈泗翰让家人给他寄了一把吉他。
当他下班回来时,只要他有时间,陈司翰就练习握钢琴。有时候,监狱里有二三十个孩子在说话、打架。他听不清楚钢琴的声音,但只要他触摸琴弦,他就会感到平静和满足。娱乐时间过去后,吉他被拿了回来,于是他把书捞出来看了看。音乐和书籍为他建造了一个避难所。
洪其俊跟陈泗翰有一些共同爱好,比如练字,有空闲的时间,可以拿笔写字时,两个人并排坐在书桌前临摹字帖。还有唱歌和弹吉他,他们自己看教材,摸索着练习和弦。
在进入少管所之前,洪在班里的成绩勉强达到中等水平。当他晚上和陈司翰一起值班时,他总是看见陈司翰拿着一本书。当他值班一小时时,陈司翰可以读一小时。他试着读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本陈司翰非常喜欢的书。他提过几次。“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意思。看了很久好像还可以。”洪看了很久,但他似乎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
推荐阅读
- 青未了|踌躇满志才是少年最美的风景
- 热评 哪有什么天才少年,只有在平凡中蜡炬成灰的父亲
- 仙侠游戏巅峰作,美少年遇上仙女妹妹,仙剑奇侠传讲了怎样的故事
- 传奇美杜莎:传奇是经典,热血是情怀!致每一位传奇少年!
- 青少年如何预防白发?
- 2011年,16岁少年欲轻生,19岁女孩主动当“谈判专家”,一吻救命
- 「康复案例」抽动症少年被治愈,眼不眨、肩不耸的感觉真好
- 南岸区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学术专题沙龙落幕
- 不能正常行走、不能端杯喝水......病痛阻挡不了临沂12岁少年的求学脚步
- 苏尚卿眼里的林乐闻是怎样的一个追梦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