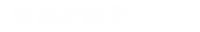我父亲工作更努力,因为他看着他爱的人离开,在方圆做了几十年的相亲。那时,医疗保健还不太发达。父亲只有一个听诊器,一个体温计,一套不同长相的医用镊子和一把剪刀,一套挂瓶软管,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这些都装在药箱里,是他行走江湖的装备。当我父亲听说有人头疼脑热时,无论晴雨,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那里。记得有一次,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腊月初十二,屋外下着大雪。看完电视剧,回到房间就睡着了。有人打电话给我父亲看一场急病。我父亲已经穿好衣服,走出了大门。我不禁感到焦虑。外面很冷,北风吹着雪。我追出去喊爸爸,你能等明天早上吗?晚上的山路已经很难走了,再加上下雪天。来叫父亲看病的人很着急,但他笑着说,姑娘,别怕。我牵着马,请你父亲骑到我家。马蹄铁被布盖住了,没有打滑。这时,我看到马蹄被微弱的手电筒光覆盖在布上。那个人说我家离这里不太远。他的孙子发高烧,很着急。之后,他帮父亲上马,父亲转身叫我进去。那天晚上,我熬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了。他连晚饭都没吃,就躺下睡觉了。别问了,这可以说明孩子的高烧已经退了,他爸爸可以这样睡。寒夜是一年四季最重的季节。我父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从那以后越来越严重。这种疾病困扰了他的余生。吃药打针都不管用。有时候疼的很厉害,我妈捏了一下暂时缓解一下。事实上,我父亲在寒冷的冬天和下雨的天气里去拜访是很常见的。就这样,父亲用有限的医疗条件对待自己无限的生命。我爸爸在业余时间总是爱看书,带着一副老花镜眼睛也不太好。那几年,因为父亲忙于各种公务,没有时间打理家庭事务,在外地干农活,母亲一个人在国内外。他的母亲一生都在干农活,沉重的土地压弯了她的腰;拉扯孩子长大,除了拉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还得拉扯二爹家的安生哥哥。生活的风霜给她的眉毛涂上了一层亮白;进入老年后,全身的疼痛让她晚年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母亲的一生就是农村妇女生活的缩影,也正是这种伟大的女性光辉孕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安生的哥哥是他二父亲家的长子。因为他的家庭离婚,他四岁的时候被寄养到我家。他呆了八年。在过去的八年里,他的父母视他为己出。十二岁时才被二爸接回平凉。二爹年轻时参军,被部队留下并安排在平凉市工作。虽然安生哥回到了亲生父亲身边,却是我父母一生的遗憾。安生的哥哥十五岁时,在一次意外中眼睛意外受伤,经过全力救治,他只能模糊地看世界。从那以后,他的母亲总是抱怨她的父亲知道她不会让安生回到他们家。
2018年夏天,父亲肿了。我的兄弟们想送他的父亲去医院。我父亲说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一种老病。我的兄弟们当然不能让他父亲走。现在社会这么好,不缺钱。我哥哥试图用言语说服他父亲,但他父亲仍然不去。没办法。我哥只能打电话给在镇医院学医的表弟,给他爸治病。表妹来的时候,他解释说要提前为父亲准备葬礼。端午节那天,父亲平静安详地离开了我们。父亲走了,葬在祖坟里。父亲一生顺风顺水,在父亲那一代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是刚正不阿的刚果,是典型的北方硬汉,但是脾气真的不怎么样。我们的七个兄弟姐妹都敬畏他的父亲。
大海在流动,事物在变化,不知不觉,今天是我父亲三年的忌日。人来人往的喧嚣,逝者的吟诵,跪在坟前的儿女,盖在坟前的纸钱璎珞,都在提醒我父亲,他真的走了。父亲躺在我面前一片空白的黄土里。每当他凝视时,画面总是交错的,从远到近,从近到远,逐渐模糊。
推荐阅读
- 英雄联盟:云顶之弈三周年纪念活动即将来临
- DNF:写在春节礼包上架前夕,请不要在找人“包春节套”了
- 男人的婚姻幸不幸福,全写在老婆脸上
- 甲骨文写在什么上面 揭秘甲骨文写在什么上面
- 李靓蕾微博 王力宏老婆李靓蕾生二胎 结婚三周年微博示爱感谢祝福
- 郭炜炜 郭炜炜为什么叫沈剑心 原来他把自己写在了剑网三里面
- 姚晨写在分手后 网传姚晨知音体分手信 经纪人称文章假的
- 王栎鑫结婚 超逗趣!王栎鑫结婚三周年表白老婆:好兄弟一辈子
- 游戏好玩,何必“3A”?浅谈国产独立游戏的发展与巧思 写在前面
- 贝克汉姆中文纹身 把爱写在身上,揭秘贝克汉姆40处纹身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