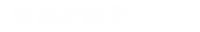杨一心 杨浦七梦|音乐:同一条河流 旧音重拾杨树浦( 三 )
杨一心:这次与伊人合作是一个较为随机的契机,我们通过朋友互相认识,一起逛书展的时候随意聊到此事便答应合作了,很难说当时为什么答应。或是因为杨浦区之于我,一直是上海我较为无知的一块区域。除了高中时候暗恋一个交大附中的女孩,于是时常会去五角场试图与她偶遇之外,可以说对杨浦是极为陌生的。另一方面,由于自己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喜欢摇滚乐,所以隐约知道杨浦在所谓“上海摇滚音乐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赵一仁:杨浦确实是我人生历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成年后,我去了杨浦北部的五角场开始读书。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洋浦”,而是觉得自己在“上海”——因为我出生在浦东川沙,而我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父母延续了他们祖先的地理认知传统,把任何一次去上海市区的旅行都称之为“去上海”。在复旦大学的几年里,我对洋浦没有任何知识和兴趣。直到毕业,我才搬到定海桥,因为我碰巧知道定海桥上一些有趣的人在做一些有趣的地方实践,这让我看到了一种研究实践/艺术研究的可能性,以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网络的可能性——这个被遗忘的杨浦区,这个上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起点,这个工人阶级抬头沮丧的地方。从此,我通过实践与一个与我的出身、工作、兴趣无关的地方建立了关系。
这些年中,我觉得杨浦有三张此消彼长又相互交叠的面孔,一张是产生于北部军区和大学中大院的精英面孔,比如他们很早就有渠道听到了国外的摇滚乐、有条件买乐器搞设备;一张是产生于杨浦东部和中部的工人面孔,他们过去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任劳任怨却精神抖擞,后来有人上访哭诉求拆迁,抑或拼命劳动多赚钱,又或赋闲在家吃低保,也有组团流氓敲竹杠,再有气定神闲养生打拳;一张是产生于寻找生存夹缝的打工面孔,他们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本地人口的日常生活和节俭消费的可能,但却在城市更新中被迫奔忙来去,永远在寻找下一个落脚处。
杨宜新:我认为这个创作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我也觉得杨浦摇滚是上海摇滚的一个开始。这部作品,或者说这部作品所聚焦的时间、地点、记忆,也是我们影像主体的一个开端,无论是创作还是其他方面。我也可以说这部纪录片/视频的创作过程才刚刚开始。从我决定与彝族合作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持久的项目。纪录片,或者说具有记录性质的视频作品,在我看来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很难准确预测拍摄周期,也很难解释它什么时候会停下来进入后期,总是从某一条线得到别人,直到一个只能被理解的点。即使真的进入后期,也会在已有的素材中发现新的线索,将作品引向另一个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过程,一个开始,一个不断变化的经历。另一方面,我也想把这部作品看作是对观众的邀请,试图让他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从而把自己带入观众的自我时间。
赵伊人:在我们研究最开始采访艺术家殷漪时,他一再提醒我们,他年轻时做摇滚乐队的意义更多限于私人成长领域,对将之公共化表示强烈怀疑——而这个开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在捡起私人记忆并将之公共化为一种历史叙述时,不将其浪漫化?以及,浪漫化有问题吗?浪漫化一种历史探寻并为其赋予尽量大的意义,是探寻者的天然倾向,是一种为自我实践辩护的倾向。如何利用这种倾向但又时时对之保持反思,需要持续探索。
杨宜新:如果要抛开创作模式和结构,只讨论这次拍摄的对象和主题,我的创作中有几点是我想重点关注的。一方面是关于记忆的干净和记忆的浪漫化。我同意对90年代浪漫的上海杨浦摇滚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我会好奇这种拒绝浪漫化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似乎总是对一些事情或记忆“浪漫化”有负面情绪?这可能会引出另一个极端,关于“记忆清洁度”的概念,即保持记忆整洁,保持距离忘记。两者都体现在我或者我身边的人身上,很少有人敢既不把回忆浪漫化,也不敢“清洗”它们。对过去的浪漫回忆与否,或者我想讨论的回忆是否主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推荐阅读
- 王者荣耀:天美出五款虎年限定皮肤,杨玉环神秘而酷炫
- 新春走基层丨杨国贵:“养牛倌”走上致富路
- 王者荣耀虎年限定皮肤海报曝光,杨玉环传说皮肤待上线
- 一个女人,真的会明知不可为却还是一心想要做第三者吗?
- 王者荣耀:天竺公主确定公孙离,女儿国国王或是杨玉环
- 王者荣耀:杨玉环首款传说皮肤确认,和金蝉唐僧皮肤成情侣限定
- 王者荣耀:不要亚瑟,拒绝杨戬,放弃钟无艳,他才是对抗路答案!
- 王者荣耀:克制马可的三位英雄,杨玉环上榜,最后一位困难重重
- 王者荣耀:杨戬带“终结”,天生多一双“抵抗鞋”
- 王者荣耀终结史诗级加强后,四位英雄受益最深,第一位竟然不是杨